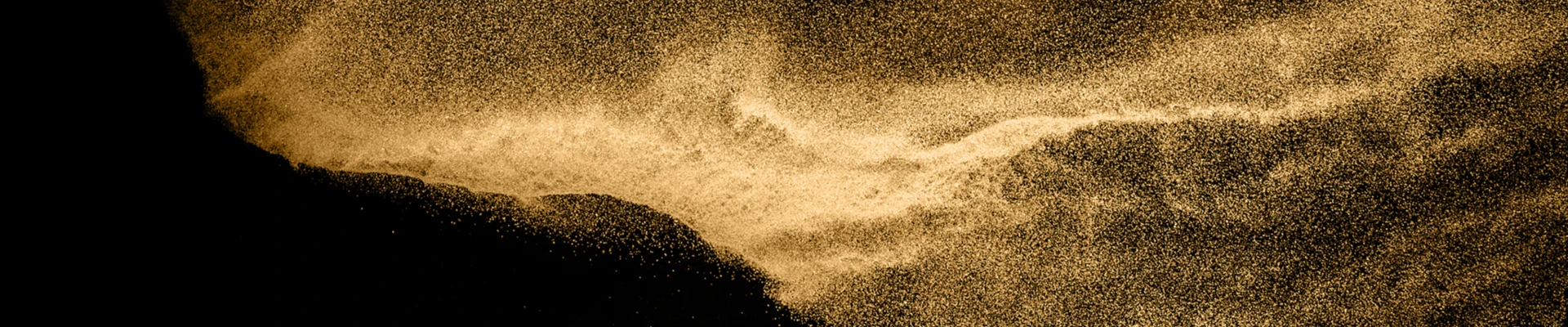保险理赔指南·确诊后,保险公司能否以不符合疾病定义条款为由免责拒赔?
1引言
随着社会的日渐发展,人们的风险意识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和家人投保了健康保险。其中,我们最为熟知常见的当属医疗保险和疾病保险。
疾病保险,根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是指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时,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的保险。保险公司推出的重疾险产品中,中对于所承保的疾病,亦分为轻症、中症和重症疾病,对应不同的赔付标准,相关疾病的定义均由双方在保险合同中予以明确。
保险公司是否应当理赔仅仅是法律后果,关键还在于疾病定义条款的性质认定和效力评价上。
因此,本文拟通过对目前司法实践的梳理,以解决如下问题:
保险合同中的疾病定义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其效力如何?
2以条款内容为例
以笔者所投保的保险合同为例,保险条款中对初患疾病的释义为:

1、2、4项条件通常并非主要争议,核心条件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为“该疾病之症状体征符合本合同的定义”。
3案例解析
温某某因“左下肢浮肿2天”入住清远市中医院,被诊断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由于温某某存在手术指征,可能出现急性肺栓塞等并发症,经过院方的沟通解释后,温某某终止妊娠,进行了包括“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等手术治疗。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属于轻症范围。出院后,温某某向保险公司发出理赔申请。
保险公司认为温某某进行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不满足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反复肺栓塞发作”的前提条件。即保险条款定义腔静脉过滤器植入术的前提为:反复肺栓塞发作及抗凝治疗无效。
此案例为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型司法案例”,并编入人民法院优秀案例选。一审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法院判决驳回温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广州中院法院改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并豁免保费。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保险合同中的“疾病释义”条款背离了一般人的通常认知和通行的诊疗标准,限缩了疾病的理赔范围,实际免除或者减轻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应视为免责条款,而被告未就该条款的概念、内容和法律后果对原告作出解释说明,上述疾病释义条款不成为保险合同的内容,故该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效力。
4具体分析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产生争议,根本原因在于保险消费者、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对于同一疾病的概念认知和判断标准存在不同。
保险公司在设计保险产品时,为提升吸引力,会将疾病承保范围尽可能扩大,为控制风险,又通过“疾病释义”方式限缩理赔范围。
医疗机构对于疾病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亦会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调整更新。
消费者通常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和保险知识,由此导致其对保险合同的合理期待与保险公司的固有理解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5观点
作者认为,对于疾病定义条款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并非是所有的疾病定义条款均属于免责条款,对其效力具体应分如下情况对待:
从形式上看,疾病定义条款均为保险人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以条款是否对诊断和赔付标准进行明确约定为标准,可分为两大类:合同制定漏洞导致未作约定、合同已作约定。
5.1合同未作约定,此种情况在专业的保险合同通常较为少见,我们需援用合同漏洞填补的补充解释技术,对双方的真实意思进行推断。
5.2合同已作约定,则根据文义是否存在歧义进行区分
5.2.1文义存在歧义
该类歧义多由于条款使用的文字含义不清、句子各成分间的关系不详等原因导致。当出现文字歧义时,我们需要通过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不利解释、诚信解释等方式,对条款的含义进行明确。
比如,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举例而言,保险合同中对恶性肿瘤的诊断约定为需“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该定义与保险业协会和医师协会共同发布的2007年第一版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保持一致。当时对于病理学检查的临床应用尚停留在传统组织病理学阶段(俗称组织块活检),组织病理检测被公认为是对肿瘤的“最后判决”,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而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细胞病理学检测(俗称细针穿刺)逐渐在医学中普及应用。近几年分子病理检测(俗称基因突变检测)又进入大众视野。
毫无疑问,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条款中的病理学检查仅指的是组织病理学检查。而随着细胞病理检测的发展和不断临床应用,如仍然坚守旧的病理学定义必然违背现时的医疗实际和公众期待。
例如,在常见的甲状腺癌理赔纠纷中,很多案例中被保险人采用的诊疗方式为细针穿刺细胞学诊断+消融手术。此种情况下,并不存在组织病理学检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病理学检查进行解释,即病理学检测包括组织病理学、细胞病理学检测。
有鉴于此,2020新修订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将恶性肿瘤的标准修改为“病灶经组织病理学检查”,并明确对病变细胞及进行病理检查的方式,属于细胞病理学检查,不属于组织病理检查。
5.2.2文义不存在歧义
此种情况下,因合同定义明确,仅存在一种解释,我们已无法适用合同的解释规则进行认定。
此时,司法审查的重点变成了:疾病定义条款的性质及其效力认定。
《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根据该规定可知,对于一般格式条款,保险人履行一般说明义务即可;对于免责条款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保险人需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
对于疾病定义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并无争议,但是是否属于免责条款,应当以疾病定义是否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是否符合一般公众的通常认知和合理期待进行判断。
例如,《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产品条款中约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应当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并考虑到医疗技术条件发展的趋势。
健康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根据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被确诊疾病的,保险公司不得以该诊断标准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理由拒绝给付保险金。
这里的“通行标准”,可以参考保险协会和医师协会共同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也包括其他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
但需要说明的是,成文类标准的修订需要程序和时间,我国也从未有正式的法律法规对通行标准的概念予以明确,因此对于通行标准的把握,仍应充分考虑现时的医学技术发展情况。
对疾病定义符合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的,应认定符合投保人的合理预期,此类条款性质上属于一般格式条款,保险人无需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对于不符合通行医学诊断标准的,应认定为免责条款,由保险人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
6免责条款的法律后果如何?
司法实践中常有认定免责条款无效、不成为合同内容和不产生效力等处理结果。笔者认为,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认定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这与《保险法》规定的“不产生效力”存在差异,前者属于合同成立阶段,后者属于合同效力阶段。可见,《民法典》对违反此项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更为严苛。由于《民法典》属于新法,且属于基本法,故《民法典》施行后,根据法律适用位阶规则,应当从新,适用《民法典》规定。由此,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如果保险人违反提示、说明义务,该条款不成为保险合同内容。
尊重医疗及保险行业实践,谨慎认定条款无效
《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
(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
(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判决疾病定义条款无效的案件,理由包括违反《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属于对正常治疗方式进行限制,应属效免责条款等。
本文认为,商业保险有别与公益性质的社会保险,即使在强调保险的风险分摊功能时,其本质仍为营利性质,本身并不承托社会保险的任何职能。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不同保险产品的定价、类型,甚至是不同保险公司的规模、承保能力均存在差异,对于相应条款的认知和设计亦会存在不同。对于商业保险的条款内容,我们不能苛以过于严格的公平、道德标准,否则,在司法实践中,亦容易出现保险兜底、劫富济贫的偏差方向。
以(2023)沪74民终365号“主动脉手术案”为例,保险合同对“主动脉手术”的定义条款与《20版疾病定义规范》中的示范内容一致,均约定“所有未实施开胸或开腹的动脉内介入治疗不在保障范围内”,但生效判决却认为,“开胸”“开腹”是对于疾病治疗方式的限制,该限制排除了被保险人对疾病治疗方式的选择权,属于无效的免责条款。
《疾病定义规范》是目前行业公认的规范,保险市场上的重疾条款,大都与行业规范保持一致,且相关规范内容的修订,亦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原银保监会)的参与和监督。
比如原银保监会办公厅于新规范实施之后就曾下发通知,要求保险公司新开发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应当符合《2020版定义》各项要求,不得再行销售不符合新要求的保险产品。在个案中,直接对定义条款作出认定并否认其整体效力,会导致个案正义与普案适用之间的冲突。
虽然在大部分案件中,认定条款无效所导致的判决结果并无差异,法院也往往出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良好的动机,但疾病定义本身有其医学专业性、合理性,司法不宜越过医疗和保险业界的既有实践,对何为公平进行主观界定。
更加妥当的做法是,在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层面予以规制,而非直接认定无效。如果保险人未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该约定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也即未订入合同。在尚未成立合同内容的情形下,更谈不上合同有效、无效的效力认定问题。
6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定义背离了现时的通用医学诊断标准,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通常认知或合理期待时,保险人应对其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否则,相应条款不能成为合同内容,保险人不得以此拒绝理赔。